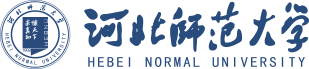|
|
我家的自留地
摘要:我家的自留地 提到“自留地”,对现今乡下的娃娃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更不用说城里的孩子了。但是他们依然可以从《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它的定义:我国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后留给农民个人经营的少量土地,产品归个人所有。 而对于我的祖辈父辈和我自己来说,它却留下了清晰而苦涩的记忆。 在令人不堪回首的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年代,广大乡村“一大二公”后给各家留下的“自留地”,虽只有可怜的几分,但那时却是乡下人用以充饥的“保命田”。 “自留地”开始是按户口划分的,几十年不变。生人不添,死人不去,姑娘出嫁后她那份也留在娘家。合理与否,国家政策就是这样制定的,乡下人也只能无条件依从。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分地时,在我家,爷爷刚刚去世(奶奶早已去世),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姐姐尚在妈妈肚子里,所以我家的“自留地”只有爸爸妈妈两个人的份。每年到了收获的季节,妈妈总是眼气那些地多的邻里,但也只有叹气的份。 懂事后的我清晰记得,当时我们生产队分给每人的口粮只有八两,平时很少沾到油水的人们饭量又格外大。所以有限的几分“自留地”里栽种什么,家家户户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都是白薯,原因只有因为它产量高,口味的好坏从来就没有想过。 在生产队上工之余,爸爸侍弄起我家那两口人的“自留地”来,精耕细作,像是女人绣花。秋天收获后,能将白薯削成片晾成薯干填补所分口粮的不足。 本来我家的“自留地”面积就小,年年青黄不接时,地里的白薯刚刚有手指般大小,就又被爸爸陆续挖出来为我们姐弟几个充饥,所以等到收获时产量比起别人家就少得可怜。如此恶性循环,我家的粮食总是接续不上,爸爸妈妈心疼我们姐弟正在长身体,粮食尽量可着我们吃,他们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到了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自留地”寿终正寝,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乡亲们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土地,过上了温饱的生活,并正在走向富庶和文明之路。 吃着自家“自留地”出产的白薯,我们姐弟几个长大成人,有的考入大学后进城工作,有的常年在外打工,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让年迈的爸爸妈妈将“责任田”转租给邻里,在家含饴弄孙,安享幸福晚年。 但是爸爸妈妈还忘不了当年自家的“自留地”,时常到那里———如今早已易主的地里走走看看。暑假孙子从城里来乡下,爸爸也会带着他们去那里玩,向他们讲述有关“自留地”的悲欢故事,但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听后却是一脸的茫然。 是呀,愿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远离“自留地”,永远远离祖辈父辈经过的苦日子。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自留地”的兴衰历史,让他们懂得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 |
|
|
在温暖的五月邮寄的花
摘要:在温暖的五月邮寄的花 我想你一定还不知道 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告诉你 我在温暖的五月 给你邮寄了一朵花 我向漫天星子借了一点璀璨 悄悄地 怕惊扰了温柔低吟的月亮 一如你当初哄我入睡的模样 我向初夏暖阳借了一缕清风 慢慢地 怕一不小心弄皱了她的衣裳 我向清晨薄雾借了一滴雨露 轻轻地 怕吓着刚刚看见一个新世界的她 尽管她经历过寒冬 已经变得自信 勇敢 善良 我在五月把那朵花邮寄给你 三月的风尚且有些料峭 四月的温度还有点偏差 六月的阳光变得有些炽热 五月正好 万物都开始苏醒 为她送上恰到好处的祝福 和着我收集的所有温暖 一起献给你 那朵在温暖的五月被邮寄的花呀 穿过北方的大河平原 穿过许多漫长的时光 来到烟雨迷蒙的南方小镇上 被一个穿着绿色工作服背着帆布包的邮递员 交到你的手上——— 致以我诚挚的思念 扮靓你最美好的模样 |
|
|
荆棘之歌
摘要:荆棘之歌 家乡的东山上 处处有荆棘的身影 直直又亭亭 顶着烈日 迎着夏雨 刷着秋风 父亲说 这是捆绑扫帚的天然绳 夏天,父亲割回来 编上几个挎篓和篮子 备秋天收获之用 秋天,父亲割回来 捆绑供我上学的“红灯笼” 嗅着荆棘上的花和叶 看到了丛中飞舞的小蜜蜂 父亲说 荆棘的生命力特别强 一直割,一直长 它的根须在石缝间穿插横行 荆棘是石头的蓬蓬勃勃的魂灵 当年廉颇老将军 背负的就是它啊 那是思过反省的坦诚 今天,在城市 我凝视着花卉市场里的盆景 我那家乡荆棘虬龙般的根啊 触发我不息的感动 |
|
|
魂断积德里
摘要:魂断积德里 我们做了两碗挂面,热了中午的剩菜。吃了晚饭,伯母还没有回来。我说: “媛媛,你一个人先在家,我跑回家,给爸留个字条就回来。” 她说:“行,放心吧。先把字条写好了再去。” 她看着我写完———“爸,伯母外出办事,我得陪小媛,可能回来晚一点。”———我快步跑回家,爸爸已经回来了,我说了陪小媛的事,爸爸说:“急人难,晚回来注意安全。”我脚下生风跑回积德里。 伯母还没有回来,天已经黑了。我们说起了《聊斋》。小媛在说“凤仙”。她忽然说:“林寒哥,现在电台在播赵因波说的《聊斋》,我们听听好吗?”我说: “好啊。” 小媛从书柜上拿出收音机,正播着《聊斋》的一段“梦狼”。 评书艺人赵因波不愧是高手,语言不急不躁,声音轻重缓急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那种诡秘的声调,制造出的恐怖气氛,无人能比……此时我们听得兴趣正浓,忽听外面轰轰两声巨响,吓得小媛一下子抱住了我。我也吓了一跳,赶紧像抱小孩一样把她完全抱在怀里,怕她吓坏了。她的脸就在我的胸前,能闻到她脸上的一点香气。我直说:“媛媛,别怕,有我在。我们离东直门近,城外经常打炮。” 我们就这样抱着。我靠在床头,一动不动。 又响了几声炮,并有噼里啪啦的巨响。确实吓人。 伯母还没有回来。小媛仰起头,脸离得太近,我直往后仰。小媛深情地说:“林寒哥,你永远都别离开我。”她把脸贴在我的脸上,我心跳得都要蹦出来了。第一次,我头有些晕。我闭上眼睛。我们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累了。小媛先起来,她说:“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很担心。本来吗,母女相依,不能分开太久。 此时,赵因波的“梦狼”早就播完了,都夜里十一点多了。小媛靠着我的肩膀像睡着了一样。我拉过一件薄毛巾被,给她盖上,我也闭目养神,不敢睡着。 北屋有一立钟,此时正敲十二点,又听街上噼啪的响。我就把小嫒轻轻抱过来,我靠着墙。这样小媛就半躺着,舒服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熬到天亮? 其实小媛并没有睡着,她似乎喜欢我们这样安静地在一起依偎着。她睡眼蒙眬地看了我一眼。我朝下看着她美丽的脸,心里涌上悲哀,好像此时是在梦中,深怕醒来,一片空虚,什么都没有了……小媛又动了一下,我感到疼……噢,是真的,就在这真假梦幻中……大门响了,伯母回来了。她看见东屋有灯,急忙进来。小媛已经坐起,趴在伯母的肩上,深怕母亲再离开。伯母像我那样搂着小媛说:“街上戒严了,差一点回不来,我走的是小胡同,遇见巡逻的比大街上的好躲。我跑过大马路时,远处朝大马路放了两枪,枪子儿擦着地面,带着火星儿,啪啦啪啦的,真吓人……”我说:“伯母,您回来了,我就回家了。”小媛急说:“太晚了,林寒哥别走啦。”伯母说:“别走啦,让媛媛跟我睡,你就睡她的床。”我说:“我跟爸爸说了,多晚我也要回去。”她们看着我坚决的样子,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又说:“好在不远,几步就到家了。” 我站起来,她们把我送出了积德里小胡同。 我快步跑回了大杂院,只有我家和鄂松山家还亮着灯。街门一响,鄂松山就喊了一声:“是生子回来啦?”我赶忙搭话:“松山哥是我,让您费心啦!”鄂大妈声音不大:“生子可回来啦!”我还是听见了,我赶忙去了大妈的小屋。大妈靠在枕头上,松山哥在给大妈洗脚。大妈说:“孩子,全院都担心,以后别回家太晚了。”我说:“大妈,让您操心,您早点睡吧。”松山哥说:“快回去吧,大爷也在等你。”我说“哎”。 (续十九) |
|
|||||||||||||||||||||||||||||||||||||||||||